诚如观点
诚如研究 | 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的采纳与采信
2025-09-12 323
早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便将电子数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加以规制,然而时至今日,以电子数据采纳与采信为核心的,电子数据可采性问题在司法实务中依然突出,即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难以评判。
例如关于第三方财务会计记账系统打印件的证据能力、证明力,不同法院便持不同态度:在成都微创医院诉陈某敬、陈某德合同纠纷案中,1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可并采纳此类保存于第三方平台的电子数据打印件;而在中山市某某制罐有限公司、伍某明等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中,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第三方平台电子数据打印件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
出现这样观点分歧的原因在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可第三方财务会计记账系统存储的数据系电子数据,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则将其视为传统书证的电子化。可见,在司法实务中对于电子数据与其他类型证据的界限、电子数据的可采性规则并未形成共识,对此本文旨在厘清电子数据在何时可以被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采纳及采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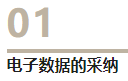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4条第1款规定明确法院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充分性进行审查,其中证据采纳围绕证据合法性、关联性展开,审查证据能力,而证据采信围绕真实性、充分性展开,审查证明效力。3电子数据的采纳也围绕证据合法性、关联性展开,除此之外还需要对证据是否属于电子数据进行界定。
(一)电子数据的界限
从表现形式看,以电子形式存在的、能作为一种证据使用的数据便是电子数据。4《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16条第2款定义电子数据为“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将传统证据类型经电子备份、电子存证而获得的数据囊括其中。然而从电子数据适用的证据审查规则来看,这类“转化型电子数据”徒有电子数据之名,实际上适用的仍是传统证据种类对应的审查规则,难以视为实质意义上的电子数据。
以区块链技术的证据化应用为例,司法实践普遍认可区块链电子存证属于电子数据,5但对区块链存证的真实性审查却十分谨慎。传统证据经电子备份、电子存证以电子数据的形式进入民事诉讼,此时即使向法庭提交电子数据的原件,法庭依然无法核实原始证据的真实性。因此,《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在线诉讼规则》)在第16条认可区块链存证上链后真实性的基础上,6在第18条第2款特别规定了上链前原始证据的真实性审查规则。7相比区块链电子存证上链后的形式外观审查及真实性推定,上链前的原始证据真实性需要当事人进一步证明,当事人不能证明或合理说明,也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法院不予确认其真实性,此种“相互印证”的证据采信方式,本质是对《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11条第2款的践行,同传统证据体系审查方式一致,8因此可以认为经区块链电子存证转化获得的电子数据并未实质适用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审查规则,而仍属于传统证据范畴,应将其视为传统证据的电子化而非电子数据。
不难发现,若数据生成、存储及其全部数据变动均发生于区块链上,此时区块链电子存证是一项原始证据,而若数据生成或部分变动发生于区块链下,经技术手段备份到区块链上,此时区块链电子存证是一项传来证据,学者分别将其概括为原生型存证、非原生型存证。9以此为分类依据,电子数据也存在原生型电子数据、非原生型电子数据,本文仅讨论原生型电子数据,而将非原生型电子数据视为传统证据。
(二)电子数据的关联性与合法性
关联性是证据能力的必要条件,与案件无关联的电子数据无法被采纳;而合法性是证据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10《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6条规定了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明确需要达到“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反公序良俗”的程度才会丧失证据资格,即轻微违法的瑕疵证据经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后仍具有证据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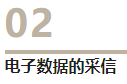
电子数据采信问题的核心在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包括电子数据载体真实性、电子数据真实性和电子数据内容真实性。11电子数据载体真实性指的是电子数据存储介质的真实性,在最佳证据规则体系下,表现为电子数据原件问题。电子数据真实性与电子数据内容真实性一体两面,指电子数据本身、电子数据表达的内容是真实的,由于电子数据容易被篡改的性质,因此常表现为真实性真伪不明时司法如何回应的问题。
(一)电子数据的原件
《民事诉讼法》第73条第1款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这是最佳证据规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与体现。电子数据的原件指最初生成后首次固定的存储介质,12这种传统原件判断标准在电子数据作为民事证据应用的场合常常发生混淆,例如在电子邮件的使用过程中,电子邮件在发送方系统生成原件,进入接收方邮箱生成复制件,即电子邮件接收方无法持有电子邮件原件,这为民事诉讼对于电子数据的证据使用带来一定的混乱。为了应对电子数据对传统原件理论的挑战,“什么是电子数据的原件”这一问题成为司法实务必须要回应的问题。
在回应电子数据原件问题的各种方法中,功能等同说与拟制原件说是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两种制度范式:功能等同说认为当电子数据具备传统原件“可识别修改”“可阅读”的功能时,即为证据原件;拟制原件说认为电子数据本身为证据原件,电子数据的精准输出物视为证据原件。13两种范式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行存在,例如《电子签名法》第5条践行功能等同范式,14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15条第2款则是拟制原件的典范。15
然而无论是功能等同说还是拟制原件说,均存在“去原始存储介质”倾向,事实上非原始存储介质在信息量方面与原始存储介质存在差别。例如,在北京华誉维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诉许侃劳动合同纠纷、16李毅诉周燕民间借贷纠纷两起案件中,17两者均声称电子邮箱被公司实际控制,案涉邮件非本人发送,若以原始存储介质作为原件,该事实情况可以通过鉴定查明,而无论是与原始存储介质功能等同的原件还是法律拟制的原件均不具备该信息,使得案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因此,这种“非原始存储介质”的原件虽然以原件或视同原件的证据地位被民事诉讼接纳,但其证明力与传统证据相比较为薄弱,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需要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来进行证据补强,否则容易使得案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最终走向证明责任分配。
所以,最佳证据规则在电子数据证据化过程中存在一定兼容性问题,正因如此,《证据规定》第93条、《在线诉讼规则》第17条不再拘泥于电子数据原件与否,转而从系统可靠性的角度直接判断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18这种以系统可靠性替代载体真实性的方式,在实务中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同时也在实质上架空了电子数据原件理论。
(二)电子数据的印证与证明责任分配
电子数据虽然容易被伪造、篡改,但伪造、篡改电子数据的行为必然产生电子痕迹,因此在理想状态下,电子痕迹理论认为电子数据具有真实性保障。19然而电子系统中充斥着各类痕迹文件,电子数据被伪造、篡改的电子痕迹很难恰好被发现,同时电子数据真实性判断需要具备很强的专业性,而司法人员并非该领域的专业人士,其在进行自由心证判断电子数据证明力时往往遇到困难。20《民事诉讼法》第66条第2款又明确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此时结合证据链条相互印证来判断证据真伪与证明力大小成为无奈之举。
若电子数据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电子数据的真实性陷入真伪不明状态,此时便需要引入证明责任分配来解决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裁判问题,但是在证明责任分配存在客观证明责任与主观证明责任的分歧,运用不同证明责任观念审理案件或导致同案不同判。在实务中,《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0条主观证明责任的援引比例远超第91条客观证明责任,21司法实践对于主观证明责任的青睐延伸至电子数据作为民事证据运用的过程中,便直接导致电子数据的采信缺乏统一标准,不同案件对于电子数据提供一方是否完成其证明责任产生分歧,继而影响实体案件的审理。
(三)电子数据的公证
在司法实务中,对电子数据进行公证能够提升电子数据被采纳的可能性,例如通常而言聊天记录截图存在被篡改、截取的可能性,在该聊天记录截图为孤证的情况下,法院通常不予认可其真实性,22但若该电子数据经过公证,即使质证方否认其真实性,法院依然可能采纳该电子证据。23即便从实质上看,公证无法消除或削弱任何质证方对于电子数据被篡改、截取的质疑。

在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的采纳和采信尚缺乏统一标准,一方面由于电子数据本身真实性难以判断,另一方面由于主观证明责任分配与客观证明责任分配存在理念冲突。但是在实务中,逐渐出现不拘泥于传统证据采纳和采信逻辑,径行判断电子数据真实性的做法,或可为电子数据作为民事证据运用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新路径。
注释:
1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川01民终10105号。
2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粤民终3007号。
3证据采纳审查证据能力,确认证据是否进入诉讼;证据采信审查证明效力,确认其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参见何家弘:《证据的采纳与采信——从两个“证据规定”的语言问题说起》,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38页、第146页。
4参见汪闽燕:《电子证据的形成与真实性认定》,载《法学》2017年第6期,第184-185页。
5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1482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民终1607号等。
6《在线诉讼规则》第16条:当事人作为证据提交的电子数据系通过区块链技术存储,并经技术核验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电子数据上链后未经篡改,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7《在线诉讼规则》第18条第2款: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可以要求提交区块链技术存储电子数据的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上链存储前数据的真实性,并结合上链存储前数据的具体来源、生成机制、存储过程、公证机构公证、第三方见证、关联印证数据等情况作出综合判断。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或者作出合理说明,该电子数据也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其真实性。
8参见刘品新:《印证与概率:电子证据的客观化采信》,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第115页。
9参见胡铭:《区块链司法存证的应用及其规制》,载《现代法学》2022年第4期,第164页。
10参见郑飞:《证据属性层次论——基于证据规则结构体系的理论反思》,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128-129页。
11参见褚福民:《电子证据真实性的三个层面——以刑事诉讼为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第123页。
12参见刘品新:《论电子证据的原件理论》,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120页。
13参见刘品新:《论电子证据的原件理论》,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121-123页。
14《电子签名法》第5条:符合下列条件的数据电文,视为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件形式要求:(一)能够有效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二)能够可靠地保证自最终形成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但是,在数据电文上增加背书以及数据交换、储存和显示过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影响数据电文的完整性。
15《证据规定》第15条第2款: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
16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沪一中民三(民)终字第1730号。
17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1257号。
18系统可靠性原则指电子数据及其打印、输出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取决于电子数据生成、传播、存储及复制的计算机及类似系统的可靠性。参见谢勇:《论电子数据的审查和判断》,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期,第119页。
19参见刘品新:《论电子证据的理性真实观》,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4期,第63-64页。
20参见刘品新:《印证与概率:电子证据的客观采信》,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第111页。
21参见吴泽勇:《民事规范的证明责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5年版,第2页。
22例如在(2023)桂民申4034号、(2024)渝民申25号等案件中,法院否认短信截图、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
23例如在(2014)二中民(知)终字第09505号、(2014)一中民终字第1994号等案件中,法院均认可经公证的电子数据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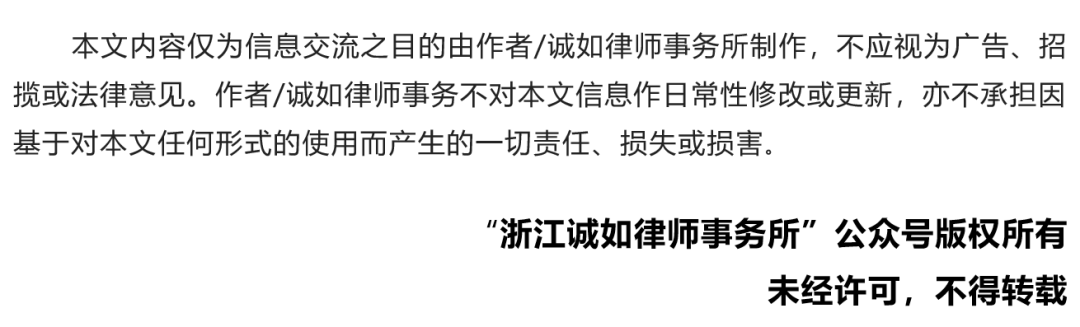
本期供稿


